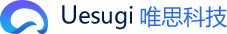饿了么与飞猪并入阿里电商事业群半月有余,互联网大厂的组织调整仍在持续:阿里合伙人团队从 26 人精简至 17 人,非业务一线岗位进一步收缩;字节 Seed 大模型技术负责人因个人问题被辞退,机器人业务负责人孔涛则离职投身创业。这些变动的背后,AI 正成为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。
过去一年,腾讯、阿里、字节、美团、百度、快手 6 家头部互联网企业均将 AI 纳入公司核心战略,累计完成至少 12 次组织架构调整,其中腾讯、阿里、字节的调整频次居前。
与 AI 创业公司相比,大厂对 AI 的投入力度与战略预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大模型融资遇冷、AI 应用尚未爆发便陷入红海竞争的当下,大厂凭借稳定的资金池、创始人的高度重视、“无上限投入” 的态度以及极具竞争力的薪资体系,持续吸引 AI 顶尖人才。然而,大厂难以完全复制 AI 创业公司的特质 —— 科研氛围的纯粹性与 AI 业务的优先级排序,始终是其面临的挑战。
此阶段大厂频繁调整架构,实则是 AI 战略推进的必然。自上而下的 “全员 AI” 第一阶段已告一段落:创始人意识到 AI 的战略价值,将其写入公司规划,加大投入并设立 AI 事业部;而自下而上的第二阶段正在进行中 —— 业务落地中遭遇实际问题,需要重新分配 AI 分工。核心人物的动向,更直接映射着高层的关注焦点。
半年内,马云五度回归阿里,每次现身都伴随着组织调整:去年 11 月蒋凡出任电商事业群 CEO 一周后;12 月 8 日蚂蚁集团周年庆上发表 “AI 时代” 主题演讲时;今年 2 月 11 日阿里宣布 “未来三年投入 3800 亿元建设云和 AI 硬件基础设施” 当天;5 月阿里打通内网、取消事业部限制次日参加阿里日活动;6 月 24 日淘宝闪购破 6000 万订单、饿了么与飞猪并入电商事业群的次日,据称参与淘宝闪购周会。2023 年起低调的马云,每次露面都与电商、AI + 云紧密相关。
退出一线五年的张一鸣,近期频繁往返新加坡与北京,参与字节 AI 核心团队 Seed 的月会。据多家媒体报道,他这段时间密集拜访科学家与创业者,深入交流 AI 议题。在此期间,字节 AI 团队高管变动频繁,张一鸣俨然成为 AI 与机器人业务的 “定海神针”。
互联网与 AI 均属劳动密集型产业,人事变动与部门更替如同企业蓝图上的草蛇灰线,循着这些线索,可窥见大厂内部真实而动态的变化。过去一年,AI 对大厂组织架构的影响呈现三大特征:
一、AI 在大厂衍生三种架构模式
互联网大厂曾离 AI 最近,创始人在该领域颇具前瞻力。但回顾发展历程,也不乏 “灯下黑” 时刻:早期设立 AI 团队,经历探索期后因产出不足逐渐边缘化,直至 ChatGPT 横空出世才再度发力追赶。
字节便是典型案例。2016 年张一鸣主导成立 AI lab,但随着他退出一线、字节重心转向站内商业化,不盈利的 AI lab 渐趋沉寂。2023 年字节重组 AI 部门时,AI lab 仍摇摆不定,今年 6 月被归入 Seed 团队。这背后既有战略决策因素,也受大厂 “水土” 影响。
与 OpenAI、Anthropic、智谱 AI 等从创立起就定位为研究型机构的 AI 原生公司不同,中国互联网大厂在二十年发展中形成了前、中、后台架构体系,倾向于在既有框架内为 AI 开辟新空间,建立 “AI 事业群” 或实现 “业务一体化”,强调落地与变现。
这种模式利弊并存:优势在于能推动 AI 与业务融合;弊端是 AI 研究员习惯的实验室协作、纯粹模型研究,与商业公司的晋升路径和考核标准存在天然冲突。例如 2023 年营收 1 亿美元的 Midjourney 仅 11 人,150 人的 DeepSeek 仅设创始人 - 小组长 - 员工三层架构,却不妨碍它们成为行业佼佼者。意识到这一点的字节,今年 3 月 18 日取消了 AI 核心团队 Seed 的 OKR 季度考核,为高薪引进的 AI 人才提供更宽松的研究环境。
经过多次调整磨合,目前大厂 AI 部门主要采用三种架构模式:
二、无上限投入与 “合并同类项” 并行
AI 研发周期长、投入大,动辄数以百亿计。大厂虽坚持对 AI “无上限” 支持,但同时也在横向合并业务,集中力量投向更具增长潜力的领域。
从近一年 AI 相关架构调整来看,阿里明显收缩核心业务,从零售、线下业务抽身,聚焦电商与 AI + 云。其他大厂也在归拢 AI 业务,合并同类项:字节大力扶持 Seed 大模型团队,同时评估 Flow 团队十余个 AI 应用的赛马结果,保留用户规模大、产品力强的,整合其余应用;腾讯将 QQ 浏览器、搜狗输入法、ima、元宝四大 AI 相关产品线迁移至 CSIG(腾讯云与产业事业群),把 AI 技术统一归于 TEG(技术工程事业群);阿里的思路与之类似,且不限于 AI 部门。
今年 3 月,阿里鼓励各业务部门积极探索 AI,CEO 吴泳铭主张在现有业务中全面实现 “AI 化”,并明确 2025 年各部门绩效将依据利用 AI 促进增长的成效评估。但随着 “1+6+N” 模式逐渐回归 “一个阿里”,这一进程可能放缓。例如 6 月初饿了么刚宣布 AI 化,随后便被并入大电商事业群。显然,在阿里内部,饿了么被归为电商撮合类业务,其与 AI 的结合优先级相对较低 —— 据了解,电商事业群 CEO 蒋凡的 OKR 中,AI 优先级排在所有指标末尾。
一个新趋势已然显现:大厂的 “无上限支持” 更具针对性,而非覆盖所有业务的 AI 化。也就是说,资源正向关键领域集中,避免重复建设。阿里 3800 亿投入计划、字节极具竞争力的 AI 岗位薪资、腾讯对 AI 短期回报的包容态度均未改变,只是:承担核心指标的部门有所调整,需要时间量化落地成效;表现不及预期的应用或团队将被 “温和” 整合,目的是刺激 AI 赋能业务,而非给出 “325” 等绩效低分。大厂正以自身方式探索 AI 团队的运行逻辑。
三、字节流动性突出,阿里调整持续,腾讯加码招聘
从 “人” 的维度看,大厂组织变化离不开招聘与离职。当前 AI 行业热度居高不下,一位人工智能从业者透露,半年前硅谷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的应届生,年薪可达 20 万美元;国内快手、腾讯、字节等大厂,算法、AI 搜索等岗位的硕士应届生月薪已涨至 4-5 万元。
大厂以高薪吸引人才,不断突破 AI 人才薪资上限。近两年,字节吸纳了众多技术大牛与成功创业者:Flow 总负责人朱骏曾是短视频产品 Musical.ly 的联合创始人,36 氪创始人刘成城(Kayden)负责字节 AI 耳机、眼镜与手机厂商的合作;去年 12 月,字节以千万年薪挖来阿里大模型大将周畅;今年 2 月,前谷歌 DeepMind 副总裁吴永辉加盟,担任 Seed 团队负责人。3 月,字节推出 “Top Seed 计划”,广纳贤才,多次为技术岗位开出数百万元年薪,进一步推高了 AI 人才的薪资水平。
然而,经验丰富的行业老兵与高薪引进的大牛,难以长期留在大厂,不少人选择跳槽或创业。据统计,已有超 20 位字节系高管离职投身 AI 创业,包括前抖音产品负责人、PICO 副总裁任利锋,前字节视觉技术负责人王长虎,前飞书海外产品负责人张涛(联合创办 Manus),前剪映商业化负责人陈冕(创办 LiblibAI)等。
阿里方面,4 月 “钉钉之父” 陈航(无招)回归后,6 月 23 日刚完成事业部大框架合并,后续调整仍在进行,具体岗位变动消息较少。据内部员工推测,回归 “一个阿里” 后,部门合并可能引发各事业部职能部门的合并缩减。
相对而言,腾讯稳定性更强,且在加码招聘。4 月 17 日,腾讯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,三年内将新增 28000 个实习岗位并提高转化录用率,2025 年将迎来 10000 名校招实习生,技术类岗位 “扩招” 力度空前。6 月校招季,腾讯推出针对技术人才的 “青云计划”,对标华为天才少年、字节 Top Seed,承诺 “薪酬上不封顶”。
无论从战略、业务还是岗位层面,AI 都在深刻重塑互联网行业。对大厂而言,面对 AI 浪潮,关键在于激发组织活力,以赢得长期竞争。
写在后面
短短一年间,各厂 AI 部门历经多次重组,大厂的组织能力仍需持续打磨。
这场从国外延伸至国内、从小厂席卷到大厂的 AI 竞赛,短期内尚未形成清晰的盈利模式,且大厂研发开支逐年攀升:2024 年字节、阿里、腾讯的投入均超 500 亿元,2025 年或将逼近千亿,其中大部分用于 AI 算力与研发人员成本。各厂 AI 业务中,仅阿里云 2022 年进入盈利周期,2024 年营收突破 1180 亿元。
大厂押注 AI 的意图明确:互联网增长见顶,它们需要通过 AI 获取新的增长机会,用前一个时代积累的红利,换取 AGI 时代的入场券。
不过,并非所有大厂都热衷于 AI 热潮,京东、拼多多、网易等企业遵循自身逻辑,发展态势良好 —— 刘强东亲自带队,带领 57 万 “兄弟们” 进军外卖市场;拼多多以千亿补贴换取用户增长;网易专注游戏与文娱领域,净利润逐年攀升。
AI 并非互联网大厂的唯一出路,但一旦选择入局,就必须接受其高度的不确定性。